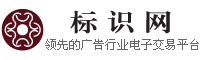不管你喜欢不喜欢,愿意不愿意,以媒体为代表的舆论监督都是符合宪法精神的一种制度性设计,也是表达公民意愿、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应有之义。同时,媒体也要善良批评,理性建议,与政府共同营造“同向效应”——
有一种说法,媒体专给政府找茬儿,哪壶不开提哪壶,索性“防火防盗防记者”。还有一种说法,记者以寻觅社会丑闻秘闻为职业,“哪里有记者,哪里就有新闻”,好像媒体和政府天然对抗。这些看法的偏颇在于:在媒介化时代来临的今天,奉行“只做不说”不仅不合时宜,而且有违政府政务公开的基本要求。作为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,只有和媒体建立一种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,通过媒体多说早说主动说,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,才能推进民主法治社会的进程。而媒体只有充分利用政府的新闻资源,才能增加自己的公信力和影响力,真正成为公众利益的守望者。
在政府(及职能部门)和媒体之间,有四对辩证统一的关系需要探究和完善。
第一,博弈中的制衡。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极易产生腐败。政府行政不仅有党的监督、上级权力部门监督和司法监督,还有社会监督,而社会监督很大程度上要靠舆论监督。不管你喜欢不喜欢,愿意不愿意,以媒体为代表的舆论监督都是符合宪法精神的一种制度性设计,也是表达公民意愿、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应有之义。
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讲过:“报刊按其使命来说,是社会的捍卫者,是无处不在的眼睛,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。”近几年来,公安部党委高度重视社会舆论和媒体对公安执法工作的监督。比如,在孙志刚事件、西安民工滞留派出所事件和来京务工人员杜宝良被罚款事件后,公安机关立即开展执法观念的大讨论,出台调整措施,以实际行动予以整改,将行政权对舆论监督权的“天然抗拒”变为“良性契合”,大大推进了公安机关向“执法为民”理念的转变。
第二,趋同中的差异。政府由人民授权,通过行使行政权生产社会公共产品,以追求公平正义的目标为己任;媒体是社会公器,是公众获取知情权并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渠道和平台,二者有着共同的价值体系。另一方面,政府与媒体所担负的社会角色各异,其运行机制、具体目标预期和内在动力又存在很大差异。特别是在社会市场化的过程中,媒体既是具有部分公共权力的舆论部门,又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产业单位,在激烈的竞争中,受收视率、订阅率和广告份额占有率的驱动,在具体新闻事件的报道中,往往出现媒体一方“踩油门”,政府一方“踩刹车”的矛盾冲突。
比如,政府及职能部门讲法定事实,讲证据和程序,讲保密原则,讲报道的社会效果与舆论效果的统一,因而不允许对事件本身做演绎和加工,将维护自身形象作为重要的价值追求;而媒体则强调公开报道,关注社会热点,追求事件报道的一步到位和深度开掘,讲求独家报道和内幕新闻,善于利用受众的激情制造轰动效应。其中也有个别媒体迎合低俗需求,将凶杀案件、恐怖画面、血腥场景、暴力事件加工渲染,将社会中的假恶丑事件和病态行为作为卖点。在湖南常德“9·1”张君特大抢劫杀人案的报道中,有些媒体就充斥着刺激感官的标题,当事人隐私的曝光,暴力崇拜的张扬,严重误导了受众。
社会前进总是伴随着矛盾积弊的暴露与解决。如何在报道中弘扬法治,既通达社情民意,又疏导公众情绪,这里有一个“把握好度”的问题。政府要坦诚面对媒体,主动接受监督;媒体要善意批评,理性建议,从而与政府共同营造“同向效应”,扶正祛邪。
第三,非对称性中的统一。政府是国家依法行政的服务部门,媒体是舆论喉舌,同处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中,媒体所具有的号召力、影响力、公信力、说服力和整合力,是政府政务工作在现代信息社会不可或缺的依赖力量,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,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,瞬间就可以“上天入地遍全球”。如果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,不能在第一时间发出政府的声音,就会被谣言和猜测左右舆论阵地,造成信息非对称的被动局面。因此,政府应充分发挥新闻发言人的作用,善于利用媒体设置议程,传播政府工作的理念和政策,增强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认知度,引导群众参与社会管理,并在突发事件中表明态度、增信释疑、降低社会风险,创造良好的政务工作舆论环境。
但在现实中,却经常出现新闻资源供需的双向不足。一方面,个别政府官员的观念上和方法上不适应政务公开的要求,往往“以不公开为惯例,以公开为特例”,不愿说,不敢说,不善说,使大量政务信息迟滞闲置,甚至在突发事件中“失语”。另一方面,一些媒体则关注腐败丑恶事件的负面报道,而对政府的议程设置诸如勤政作风、便民措施、亲民形象、政绩成果的报道缺乏积极性,“好事不出门,坏事传千里”。有时将个别变成一般,将个案泛化,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损伤。此外,对一些在侦的刑事案件、尚未终审判决的案件,还会出现舆论定案、